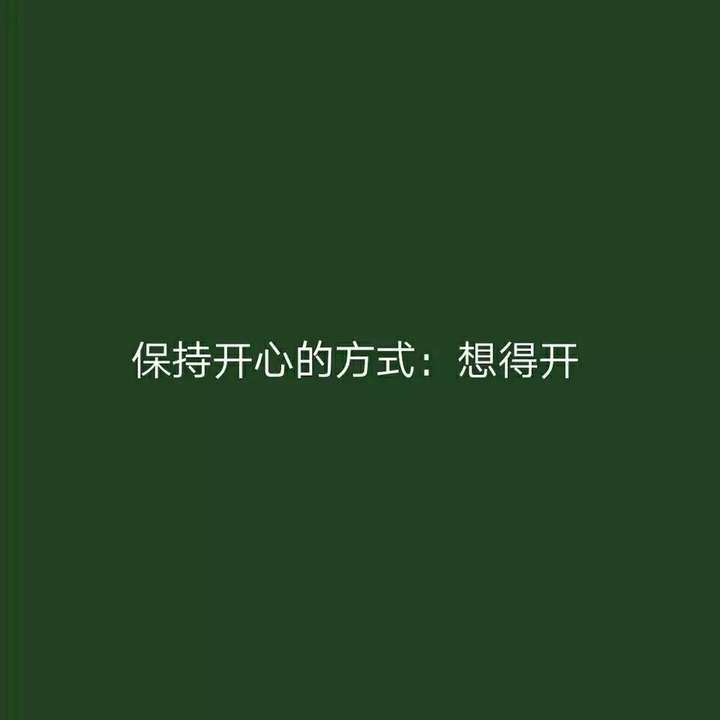9 争吵
晚上他们拥抱在一起。小恩柔软的裸体在他的怀抱里蠕动,他抚摸和亲吻着她,然后反转过身体要她。做爱是他们生活里最重要的内容。可以连续地做爱,一直到她的身体出血。他不清楚这剧烈的欲望来自何处。他们在大铁床的白床单上做爱。这惘然的激情让人茫然不知所从。
他说,小恩,你不要再吃药了。
小恩说,不吃的话,我就会怀孕。
我就是想让你有个孩子。
为什么?
有了孩子你就不会走了。
有很长一段时间,这的确是他心里最强烈的一种推动着欲望的力量。他看着小恩洁白赤裸的身体和漆黑的长发,她的脸有一种情欲的创伤和妖艳。她对他说,我已经动过三次手术了。如果再有孩子,再做手术,我会一辈子残废。
他说,为什么要再动手术。我要这个孩子。我也要你。
她安静地看着他。她说,我还不能要。我还需要时间。
她渐渐开始有一些朋友。也有了固定合作的业务。每周出去一两次。
一早起来,洗澡化妆,然后穿着干净宽大的布衬衣,粗布裤子和棉大衣,背一个黑色的帆布大包带着笔记本电脑出去。常去国际大厦一带谈公务,回来后就对他说,那里有北京最有气质的女人们。打扮得比上海女人还精致。
她是注重生活质量的人。化妆品一律是日本和法国的原装进口。光是不同的睡衣就可以买上许多,一件件挂了香薰袋子吊在衣橱里。当然这些她全都是自己购买。她从不问他要钱。除了家里的费用。
她的收入是不稳定的,但一旦有收入就会是一大笔。可能会是他工作半年或一年的全部。即使如此,她依然要他负担家里全部的杂费。她说,这没有什么二话,你是男人。再没有钱,你也得负担责任。当然如果你要AA制也可以。但如果AA制,我们就分房间,各不打扰。
他说,我是男人,也有收入。我们在一起,我肯定会承担责任。但你要说清楚最后一句话是什么意思。
就是该用感情的时候用感情,该用金钱的时候用金钱。不要在该用金钱的时候用起了感情,而在该用感情的时候用起了金钱。她的眼神很漠然。
他说,那你心里对我有没有感情呢?
她看着他,不回答。
他说,你为什么要和我在一起。仅仅是为了找一个男人陪着你?
她说,找个男人要那么费劲吗?要千里迢迢带着大包小包飞过来?
他沉默,不再说话。
10 伤口
那天两个人准备去超市买加湿器和电暖器,附带买了一些蔬菜和熟食。
结账的时候是小恩付的钱。两个人各自拎了大塑料袋,准备回家。刚走出超市大门,小恩就对他说,加湿器和电暖器不能算在你给我的杂费预算里。你要还给我800块钱。
他刚好因为借给朋友钱,这个月工资已经所剩无几,准备下个月给她。嘴巴里却对她开玩笑,为什么要还你。我不还了,这些钱你来出。
凭什么。我在家里做菜烧饭,做家务,还买床单被子瓷器鲜花,我什么时候对你计较过那些?你现在连买些小电器都不肯。那可是我们共同用的,又不是我一个人用。
他说,谁让你买床单杯子瓷器鲜花了?我的生活本来就很简单,不需要像你这样要求高。
我要求高?家里布置得好看难道你没有享受到吗?无能的男人才为自己找借口。
他没有想到她会这样劈头盖脸地发作。而且说话的时候根本无视一个男人的自尊。他说,我一开始就告诉过你,我不会是你需要的那种男人。我也没钱。
没钱你就去死。她突然把手里装满了鸡肉,牛奶,苹果的塑料袋子往地上一放,转身就跑。他的手上也拎满了东西。旁边已经有人围观。他的怒气控制了他,已经无法思想。他也放下手里的东西,跑上去追她。她在满是车流的大街上简直是发疯一样地跑。汽车尖利的紧急刹车声响起来,司机探出脑袋来咒骂。
在一个拐角他抓住她。他紧紧地扭住她的手臂。她挣扎着,用手去扯他的头发。他劈头就给了她三个耳光,打得她晕头转向,差点跌倒。他气得浑身发抖。他说,你这个疯子。
她的确如同疯了一样,扑上去狠狠地咬住他的脖子。他痛极放手。一放开手,她就像一条鱼一样滑开。她再次离开他飞快地跑走。
一直到天黑她还没有回来。他打她的手机,一直在响,但她不接。他固执地一遍又一遍地重复,直到最后传过来的是关机的提示。她不肯和他说话。
他在家里心神不宁。打开电脑玩游戏,想控制自己的情绪,但无法奏效。他发现自己的手指居然一直是在微微地颤抖着。他看着墙壁上她的照片,那些用陈旧的木相框框起来的黑白照片。她甜美脆弱的花朵一样的容颜。他每次凝望那些照片心里就会难过。虽然不明白为何会难过。
但是那一个晚上,他看清楚了。他在她的脸上看到始终没有愈合的创伤。她是一个赤裸的疼痛着的伤口。她的灵魂是他没有触摸到的喜欢躲在黑暗里的孩子。
他每过5分钟就打一次手机,虽然回复他的是一次又一次的关机提示。北京是这样大而无当的一个城市,她如露水一样蒸发。她到底会去往何处。
深夜12点钟的时候,他终于打通了那个手机。她接了电话。
小恩,原谅我。我错了。他听到自己软弱而焦虑的声音。他说,你到底在哪里?
电话里很嘈杂,可以听到汽车的喇叭声,音乐和旁人激烈的话语。小恩的声音却很温和,懒懒的,并不介意。她说,我在吃东西。
你在哪里?告诉我。我过去接你。
不。不要你过来接。我自己会回来。一会儿就回来。
小恩,告诉我。你不要再惩罚我。是我不好。
她说,我在东直门吃麻辣龙虾,喝了酒,好像醉了。站不起来。
你等着。你千万别乱跑。我马上过来。
他跑下楼梯的时候,看到外面的天空下着雪。寒风刺骨,大朵干爽的雪花寂静地飘向黑暗的城市。他在街上拦了一辆TAXI。路上有恋人把衣服盖在头上,紧紧拥抱着走过去。
他想起他们曾经在电话里的对话。
11月初就下雪吗?上海1月份才有雪。一个晚上就停了。
你会在北京看到大雪纷飞的。不要担心。
那时候他们还没有同居在一起。那时候他不会想到自己会动手打她耳光。
很容易就在他们以前去过的小餐馆里找到小恩,她一个人占着一张桌子,上面放着空的酒瓶和满满一大盆龙虾壳。她支着头,趴在桌子上,眼神游离。看到他,轻轻地笑。
我吃了60只龙虾。辣得嘴唇都肿了。她噘起嘴唇给他看。唇角都是油腻的污渍,果然是红艳艳的,像肿胀的花苞。
他看到的是她脸颊上,他留下的手指印。还有她嘴角的伤口。
你怎么可以吃那么多龙虾,你会吃伤的。他心力交瘁。我们回家吧,小恩,我求你。
好。回家。她摇晃着起身,撞得桌子移动。他扶住她。她看过去过分地平静了。他不知道她这一晚上都做了什么。
街上已经大雪弥漫。他们拦了一辆车。她在出租车上把头埋在他的怀里就睡着了。
大约是凌晨3点左右,他突然惊醒过来。看到小恩赤裸着身体坐在大铁床的床尾,她用手抓着黑色的铸铁栏杆,长发披垂下来,遮住了她的脸。
小恩,你在做什么。他在黑暗中抱住她冰冷的肩头,摸到她脸上的泪。她在哭。
她说,嘴唇上很痛。所以去吃龙虾,想让它被辣得更痛,感觉会木一些。但现在痛得睡不着了。
你怎么可以去做这样的事情。你为什么要这样对待自己。
你老实告诉我,你有没有打过叶子。你有没有动过她一根手指头。
不要再问这种问题了。小恩。
你说。你要告诉我。
我和她根本就没有住在一起。我们是在学校里认识的。
你不会打她。你对她的感情,比我深得多。
这是你自己在这么想。
我那么远过来,和你在一起。
我知道。我知道。小恩,我求求你,不要再胡思乱想。
他抱住她。他感觉到自己眼睛里的泪水,没有触觉地流下来。然后在空气中消失。心里是有失望的。对自己无能为力的失望。对这份感情的痛苦的失望。觉得自己要死过去一样。
这个任性的脆弱的受伤的女子。她像一道伤口,出现在他的生活里。而他们彼此本可以互相拒绝的。他们都不安全。
11 打架
她决定去找工作上班了。
呆在家里容易得忧郁症。她对他说,我要见见陌生人,和他们在一起,这样就不会想起你对我的不好。
他也觉得她出去工作比较好。有时候下班回来,看到她一个人在家里,空气里都是冰冷的寂静,很难想象她是如何地把一天,硬生生地支撑下来。没有对话。没有气味。没有温度。
她的性格是不适合独处的。
可是我一个人在家里已经停留了很长时间。我很久很久没有出去工作了。她说。
找工作是要费点神。她想做美术设计。网站,报纸,杂志,公司都可以啊。她说。可是一家家地出去跑,结果却都不好。不是她觉得工资低,公司规模不够大,就是对方觉得她没有北京户口,态度不太明确。在一个月里面,她每天都往外面跑。神情奔波而憔悴。也不再在家里做饭、浇花、有那份闲情逸致。有时候很晚回来,头发上有烟草的混浊味道,往床上一躺,对他也没有话说。
他能感觉到她的心里有一股暗流,在危险而压抑地涌动。
果然。他发现她后来已经不再找工作,她只是每天晚上泡在三里屯一带,找个酒吧喝到半醉,才衣衫褴褛地回家。
他当然要制止她。他说,小恩,我不能容许你再去酒吧。
她说,你有什么资格。可笑。我难道连行动的自由也没有吗?她又是那种劈头盖脸的架势。
他说,如果你心里有什么不满,你直接说出来。
我讨厌你。
他想他还是能够控制自己的。直到她的手伸出来揪住他的头发。
她是有暴力倾向的人。他压抑了太久的愤怒再一次如潮水决堤。两个人纠缠在一起厮打。从床上到地上。没有穿衣服,赤身裸体。他把她按倒在冰冷的地板上,一下一下地揍她。他能感觉到自己脑子里的空白。什么都没有了。只有机械地运动着手臂的意识。她用手护住自己的头和脸,一声不吭,蜷缩在地上,任他又踢又打。直到他疲倦。
每一次都是相同的。他很快恢复了思维,脑子里清醒过来。不再是空白,后悔和恐惧再次如阴影一样笼罩了他。
她慢慢从地上爬起来,赤裸的身体上是尘土的污迹和红色的淤痕。长发散乱,被汗水粘在脸上。她的脸上居然有微笑。那缕冷漠的微笑因为她嘴唇边的鲜血,显得诡异。
他说,我知道你喜欢这样。你是被虐狂。
她不说话,爬到床上坐在那里。她一直在笑。
他走过去,抱住她。他紧紧地抱住她,把脸贴在她的脖子上。她的脖子上也是血。
小恩,为什么?为什么我们会这样?
他轻声地疑惑地自言自语。他问她。他想起叶子的脸,那张在明亮温暖的阳光下像花朵一样绽放的脸。那时候他20岁。他第一次爱上一个女孩子。他是真挚地深切地爱过她。直到最后她离开他嫁给了另外一个男人。
他曾经猜测过自己心里爱的能力还留下多少。他是否还能够继续走下去,把感情托付给另外一个陌生的女子。
他突然明白有些东西是无法修复的。他心里明亮的东西有大部分已经被阴影覆盖。那是一些自私的愤怒的寒冷的东西。从遥远南方过来的小恩,来到他的身边。他们在彼此激发。激发深藏着的阴影。
他们又开始做爱。小恩顺从地让他摆布。她没有声音也没有表情。她像一只彻底被破坏掉的玩具。甚至不再像以前那样提醒他及时抽身。他觉得自己太困了。贴着她的身体就睡了过去。
睡了一会儿,他被她摇醒。她说,我做梦了。刚刚做了一个梦。
她的神情看过去像一个睡意朦胧的天真的小女孩。他说,是噩梦吗?
不。我看到我们去订婚。排着队。很奇怪,不是结婚只是订婚,却要排那么长的队。我的手里还抓着粮食,好像是一把米。
你想嫁给我吗,小恩?他问她。
你要我嫁给你?
我想娶你。你相信我。
她没有说话,她又闭上了眼睛。她唇角和脖子上的血迹已经凝固了。她不让他擦干。她阻止他的姿态非常强硬。她又睡着了。
12 为什么不能这样做
第二天他一早起来去上班。
她还在熟睡。出门之前,他想给她留一张条子。他写:小恩,晚上我们一起出去吃晚饭。原谅我。我以后再不会这样做了。你要相信我。
写完之后,看了一会儿,又随手把它撕掉。是。他不能让她看到他心里的软弱和恐惧。即使她已经融化在他的生活里,几乎不可分割。
他关上铁门下楼。因为脖子上有她指甲抓伤的血痕,他找出了一条围巾遮盖上。
还是在下雪。路上的雪全冻住了。他仰起头吸了一口凛冽的空气。他想,他还有工作,他还有一个现实正常的世界可以面对。他还有一个出生和长大的熟悉的城市。而小恩,她什么都没有。
他下了决心要对她好。
一整天上班他心神不定。常常无缘无故地掉下文件或碰到椅子。中午吃饭休息的时候,他拨小恩的手机,她没有开机。应该还是在睡觉。下午他一直在寻找机会想早点回家。可是会议一个连一个,始终无法脱身。下班之后,上司又过来通知,因为他过生日,要邀请整个部门的同事出去吃饭。
不可推脱,于是又和一大帮同事们去了星期五餐厅。抽空打手机给小恩,依然是关机。怎么会这样呢。平时她为了方便客户联系到她,常常24小时开机。不敢喝太多酒,好不容易挨到11点左右,聚餐终于结束。
他马上打的回家。他突然担心她不会在家。可能又出去流连在酒吧。如果这样,那么他要赶过去一家一家地找,直到把她找出来。在上楼的时候,他甚至听到自己的心脏激烈跳动的声音。一下一下,跳得是那样的痛。
门一打开,房间里是寂静的空气。他走到房间里一看,小恩还睡在床上。他呼出一口气,说,懒虫,你有没有吃过饭呢,不会一整天就躺着吧。走过去一看,她的脸色苍白,额头上还冒着冷汗。
他把手捂在她的脸上。他说,病了?身体不舒服吗?
她闭着眼睛,只是疲倦地摇摇头。我要休息一下,明天会好一些。
他说,为什么会这样。告诉我,小恩。
她冷漠地看着他。她说,今天我去医院了。我做了手术。
你怀孕了?
是的。一个月前。
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?你怎么可以这样做?
我为什么要告诉你。我又为什么不能这样做。她轻而坚决地推开他的手。
13 不知何处是家乡
有很长一段时间,他们彼此小心翼翼,突然客气了很多。
她很快就恢复了往日的活力,开始在家里忙碌。他无法测量她所遭受的身体上的伤痛。
她曾经对他说过,她已经做过三次手术,如果再做,会有残废的危险。她说话的时候神情是严肃的,带着请求。是。他知道。她对伤痛的害怕是深切而真实的。
可是她什么都不对他说。
星期六的时候,他们决定去爬山。很久他没有带她出去玩。她到了北京之后因为人生地不熟,几乎从不曾去体会这个城市。
他们坐地铁到苹果园终点站,然后转车去八大处。
红叶早已经凋落。山间只有疏朗的树枝和满地酥脆的落叶。他们爬得很慢。到了适合观望风景的地方就停下来歇息。小恩靠在岩石上晒太阳。阳光很清淡。有黑色的鸟在树梢发出咔咔的奇怪声响。它张开翅膀,顺着山谷的坡度,一路滑翔下去。自由自在。北方的山,在冬天只有肃杀的凛冽。
他们看到一对年老的夫妇,穿着球鞋和运动装,随手拎着大袋子收集空的矿泉水瓶子。
小恩看着他们说,他们在一起应该很久了。
是的。大部分夫妻还是会在一起很久的。他说。他们已经下山。小恩突然觉得身体不适。她常会觉得疲倦。在山间穿越一片树林的时候,突然看到黄昏的阳光从树枝间穿越过来,金色的光线跳跃。像是电影里的某个场景。
厚厚的落叶,踩上去已经发不出声音。松鼠晃动着大尾巴,悄悄地爬上松树。不知名的美丽大鸟,低声鸣叫着惊跑。蓝得发紫的羽毛。
他们走到了山下。有暮色笼罩的小寺庙。点着的香散发出淡淡的味道。洁净的红砖和青石路面。柿子树上垂挂着最后几只红色的烂熟甜柿。粗壮枝干的中国玫瑰已经开得凋谢。
他们在庙里流连。墙上有各种字画。她一直停顿在那里看着一段话。他走过去,看着那里写着的是憨山大师的一段醒世咏。小恩说,最后两句话写得太好了。她回过头去看他,眼睛里有泪水。她念给他听,她轻轻地说,顷刻一声锣鼓歇,不知何处是家乡。
他突然发现自己停顿在那里无法动弹。他握住她冰冷柔软的手。他说,小恩,我需要你。
她淡淡地微笑。可是你了解我吗?我的过去你一无所知,我的未来你也无法把握。你所能做的,其实只要是对我好一些就可以。因为我一个人来到这里。
14 离开
3月的时候,她找到了工作。
是在广州。一家很大的知名设计公司。
她说,我必须得去工作。我累了。我一个人很寒冷。
他知道肯定要放她走。看她慢慢地开始收拾自己的行囊。她只带走她的书,衣服和那一大堆旧的随身物品,包括小熊和瓷杯子,而把所有值钱的新购置的东西都留给了他。
他说,你还回来吗?
回来。过年的时候就回北京来看你。在上海我已经没有家了。在北京就留一个家给我吧。
他看着她。他不相信她。他相信她一到新的地方就会抛弃她记忆中所有的往事。她只恋物不恋人。她早就这样对他说过。
他送她去机场。她还是背着她来时的包。她喜欢的日本包,褐色的麂皮,摸上去绒毛会一层层地倒下去。名字叫Tokyo。她穿着旧牛仔裤,跑鞋,厚的纯棉T恤,头发长了许多,凌乱地贴在脸上。
她看着他。她的脸上又有了那种天真甘甜的笑容。她像一朵干燥的花恢复了水分。在他身边的时候,她的冷漠和愤怒曾是这样的多。
她背了包起来准备进候机厅。他看着她背上一个包,手里分别拎着两个,倔强而坚持地用力支撑自己。她一贯如此。
她转身对他挥了挥手,然后消失在拐角处。
15 原来也就这么多
他们同居的日子一共是7个月零9天。
他把房子退了。准备回家。他要把剩下的东西都搬到家里。
最后一天收拾东西的时候,搬家公司的大卡车已经停在楼下。
他作最后的检查。在卫生间的瓷砖里看到一缕头发。他捡起来看,很长的漆黑的发丝,应该是小恩洗头的时候遗留下来的。
他想,这才是她留给他的惟一的东西。
他们彼此之间有过的,原来也就这么多。
生命是一场幻觉。
就这样,《七个月零九天》的故事结束了。
‘所有男生在发誓的时候都是真的觉得自己一定不会违背承诺,而在反悔的时候也都是真的觉得自己不能做到。’ 那如果做不到,还不如不要说。